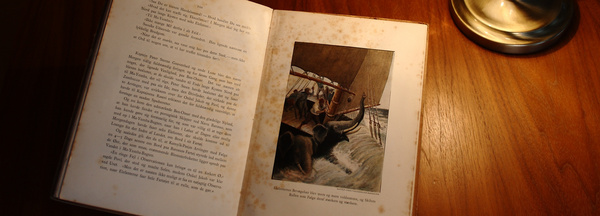йӘ„йҳідјјзҒ«пјҢеҚ•и°ғиҖҢжӮІдјӨзҡ„жӣІи°ғеңЁзӘ’жҒҜзҡ„з©әж°”дёӯеӣһиҚЎпјҢдёҖйҒ“йҒ“иөӨиЈёзҡ„й»‘иүІи„ҠжўҒдёҠеҸҜд»Ҙжё…жҷ°ең°зңӢеҲ°жҳ”ж—Ҙзҡ„йһӯз—•пјҢдёҖж Әж Ә并дёҚй«ҳеӨ§зҡ„жӨҚзү©дёҠз»Ҫж”ҫзқҖдә‘жңөиҲ¬иҪ»иҪҜзҡ„зҷҪиүІзәӨз»ҙгҖӮиҝҷжҳҜдәә们жүҖзҶҹиҜҶзҡ„19дё–зәӘеҗҺеҚҠеҸ¶зҫҺеӣҪеҚ—йғЁжҷҜи§ӮпјҢеҶ…жҲҳзҡ„з»“жқҹ并没жңүз»Ҳз»“иҜҘжҷҜи§ӮдёҠеҸ‘з”ҹзҡ„ж•…дәӢпјҡжЈүиҠұдҫқж—§жҳҜеҲ©ж¶ҰжңҖдё°еҺҡзҡ„дҪңзү©пјҢйқһиЈ”зҫҺеӣҪдәәи§ЈйҷӨдәҶеҘҙйҡ¶зҡ„иә«д»ҪпјҢдҪҶжҳҜж— жі•ж‘Ҷи„ұз»ҸжөҺдҫқйҷ„зҡ„жһ·й”ҒгҖӮеҘҙйҡ¶еҸҳжҲҗдҪғеҶңпјҢ他们еӣһеҲ°зҶҹжӮүзҡ„жЈүиҠұз§ҚжӨҚеӣӯдёӯпјҢжңәжў°ең°йҮҚеӨҚж—§ж—Ҙзҡ„е·ҘдҪңпјҢжҢЈеҫ—д»…еӨҹи°Ӣз”ҹзҡ„еҫ®и–„и–Әж°ҙпјҢиҮӘз”ұжӯўдәҺдёҖзәёж–Үд№ҰгҖӮзӣҙиҮі1892е№ҙпјҢиҝҷзүҮжҷҜи§Ӯзҡ„ж•…дәӢдёӯеҮәзҺ°дәҶдёҖзҫӨж–°зҡ„еҸӮдёҺиҖ…гҖӮе®ғ们иә«иәҜеҫ®е°ҸпјҢиЎҢеҠЁиҝҹзј“пјҢдҪңдёәдёӘдҪ“еҸҲдёҚе ӘдёҖеҮ»пјӣдҪҶжҳҜе®ғ们жӢҘжңүејәеӨ§зҡ„з№Ғж®–иғҪеҠӣпјҢдёҖеӯЈеҸҜд»Ҙз”ҹдә§200дёҮеҲ°1200дёҮеҸӘеҗҺиЈ”пјҢи¶ід»ҘдҪҝд№ӢжҲҗдёәдёҖж–№йңёдё»гҖӮиҝҷзҫӨж–°и§’иүІзҡ„еӯҰеҗҚдёәAnthonomus grandisпјҢиӢұж–Үдҝ—еҗҚеҲҷжҳҫиө«еҫ—еӨҡвҖ”вҖ”boll weevilпјҢдёӯж–Үдёә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гҖӮ
иҝҷдәӣйЈһиҷ«зҡ„ж•…д№ЎдҪҚдәҺеҗҺжқҘжҲҗдёәеўЁиҘҝе“Ҙзҡ„еңҹең°дёҠпјҢдәәдёәзҡ„еӣҪ家иҫ№з•Ңйҡҫд»Ҙйҳ»йҡ”е…¶жүҮеҠЁзҡ„еҸҢзҝјгҖӮжҳҶиҷ«еӯҰ家жҷ®йҒҚзӣёдҝЎж—©еңЁеҫ—е…ӢиҗЁж–Ҝе·һејҖе§ӢеӨ§йқўз§Ҝз§ҚжӨҚжЈүиҠұд№ӢеүҚпјҢ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дҫҝе·ІжқҘеҲ°зҫҺеӣҪпјҢдҪҶжҳҜе…¶зңҹжӯЈиў«зЎ®и®Өзҡ„ж—¶й—ҙжҳҜ1892е№ҙпјҢеҪјж—¶пјҢеҫ—е…ӢиҗЁж–Ҝзҡ„жЈүиҠұдә§йҮҸдёә150дёҮеҢ…пјҲжҜҸеҢ…500зЈ…пјүгҖӮжЈүиҠұз»ҸжөҺзҡ„й»„йҮ‘ж—¶д»ЈеёҰжқҘдәҶ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зҡ„й«ҳе…үж—¶еҲ»пјҢеҲ°1904е№ҙпјҢиҘҝеҘҘеӨҡВ·зҪ—ж–ҜзҰҸжҖ»з»ҹеңЁе…¶еӣҪжғ…е’Ёж–Үдёӯе®Јз§°пјҢзҫҺеӣҪзҡ„еҒҘеә·дёҺе®үе…ЁжүҖйқўдёҙзҡ„жңҖеӨ§еЁҒиғҒд№ӢдёҖжҳҜвҖңдёҖз§ҚдёӯзҫҺжҙІзҡ„жҳҶиҷ«пјҢеңЁеҫ—е…ӢиҗЁж–ҜеӨ§иӮҶз№Ғж®–пјҢдёҡе·ІйҖ жҲҗе·ЁеӨ§з ҙеқҸвҖқгҖӮд»Һ1892е№ҙеҲ°1904е№ҙпјҢ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дёҚж–ӯеҗ‘еҢ—еҫҒдјҗпјҢзӣҙиҮіжҠөиҫҫеӨ§иҘҝжҙӢпјҢеҚ йўҶж•ҙдёӘеҚ—йғЁжЈүиҠұе·һпјҢж—¶дәәе°Ҷд№ӢжҜ”дҪңеҶ…жҲҳеҗҺжңҹи°ўе°”жӣје°ҶеҶӣеҗ‘еӨ§жө·зҡ„иҝӣеҶӣпјҢвҖңдҪҶжҳҜеёҰжқҘжӣҙеӨ§зҡ„жө©еҠ«вҖқгҖӮзҫҺеӣҪеҶңдёҡйғЁе’Ңеҗ„е·һеҶңдёҡйғЁй—Ёзҡ„专家гҖҒжҳҶиҷ«еӯҰ家гҖҒеҢ–еӯҰ家гҖҒз»ҸжөҺеӯҰ家зә·зә·жҠ•е…ҘеҲ°еҜ№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зҡ„з ”з©¶еҪ“дёӯпјҢдёҺжӯӨеҗҢж—¶пјҢиҝҷдәӣ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д№ҹеҮәзҺ°еңЁеҚ—йғЁж°‘й—ҙж•…дәӢдёӯз”ҡиҮіжҲҗдёәдё»и§’гҖӮе®ғ们被称дёәзҫҺеӣҪеҺҶеҸІдёҠжңҖжҳӮиҙөзҡ„жҳҶиҷ«пјҢжҳҜеҚ—йғЁжЈүиҠұз§ҚжӨҚеӣӯдё»зҡ„жўҰйӯҮпјҢеҚ—йғЁиө–д»Ҙз”ҹеӯҳзҡ„жЈүиҠұз»ҸжөҺзҡ„зҳҹз–«гҖӮжҚ®з»ҹи®ЎпјҢиҮӘ1892е№ҙеҲ°20дё–зәӘжң«пјҢ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е…ұ摧жҜҒдәҶж•°зҷҫдәҝзЈ…жЈүиҠұпјҢйҖ жҲҗжҚҹеӨұиҫҫдёҖдёҮдәҝзҫҺйҮ‘гҖӮ
дёҚиҝҮпјҢд№ҹжңүдәәзңӢеҲ°дәҶдјҙйҡҸ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зҡ„еҲ°жқҘиҖҢеҮәзҺ°зҡ„еҘ‘жңәгҖӮ1919е№ҙпјҢйҳҝжӢүе·ҙ马е·һзҡ„еӣ зү№жҷ®иҺұж–ҜеёӮеңЁе…¶еёӮдёӯеҝғз«–з«ӢдәҶдёҖе°ҠеёҢи…ҠеҘізҘһзҡ„йӣ•еғҸпјҢ全然еӨҚеҸӨзҡ„иүәжңҜпјҢж—Ғиҫ№зҡ„зҹіеҲ»еҚҙеҶҷйҒ“пјҡвҖң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зәӘеҝөзў‘пјҢ1919е№ҙ12жңҲ2ж—ҘгҖӮи°Ёд»ҘжӯӨеҗ‘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д»ҘеҸҠе…¶дҪңдёәз№ҒиҚЈзҡ„е…Ҳй©ұиҖ…жүҖеҒҡзҡ„дёҖеҲҮиҮҙд»Ҙж·ұжІүзҡ„и°ўж„ҸвҖқгҖӮ1949е№ҙпјҢеҘізҘһеҸҢжүӢжҚ§иө·зҡ„еңЈзў—дёӯиў«ж”ҫе…ҘдёҖеҸӘйҮҚиҫҫ50зЈ…зҡ„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еЎ‘еғҸгҖӮе®ғжүҖи®Іиҝ°зҡ„жҳҜдёҖдёӘ全然дёҚеҗҢдәҺжөҒдј еңЁеҚ—йғЁжЈүиҠұз”°й—ҙзҡ„ж•…дәӢгҖӮеңЁиҝҷдёӘйҳҝжӢүе·ҙ马еҗҚдёҚи§Ғз»Ҹдј зҡ„е°ҸеҹҺпјҢжЈүй“ғиұЎйј»иҷ«1918е№ҙзҡ„еҲ°жқҘдҝғдҪҝ他们иҪ¬еҗ‘иҠұз”ҹзҡ„з§ҚжӨҚдёҺз”ҹдә§пјҢиҝӣиҖҢжү“з ҙдәҶеҚ•дёҖз§ҚжӨҚзҡ„еҶңдёҡж јеұҖпјҢејҖе§ӢдәҶеӨҡж ·еҢ–дҪңзү©з»ҸжөҺгҖӮжӣҙжңүеҺҶеҸІеӯҰиҖ…и®ӨдёәпјҢе®ғ们жҳҜзҫҺеӣҪеҚ—йғЁжЈүиҠұз»ҸжөҺжҒ¶жҖ§еҫӘзҺҜзҡ„з»Ҳз»“иҖ…пјҢйқ©е‘ҪжҖ§ең°йҮҚз»„дәҶзҫҺеӣҪд№Ўжқ‘з»ҸжөҺпјҢжҺЁеҠЁдәҶеҶңдёҡзҡ„зҺ°д»ЈеҢ–пјҢ并且жҺЁеҠЁдәҶ20дё–зәӘ20е№ҙд»Јй»‘дәәеҗ‘еҢ—йғЁе·һзҡ„еӨ§иҝҒ移пјҢеҗҺиҖ…еҪ»еә•ж”№еҸҳдәҶзҫҺеӣҪзҡ„ж—ҸиЈ”ең°еӣҫе’Ңж–ҮеҢ–зӨҫдјҡеҪўжҖҒгҖӮ
ж— и®әжҳҜж—¶дәәеҜ№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еҜјиҮҙзҡ„зҒҫйҡҫзҡ„жҸҸз»ҳпјҢжҠ‘жҲ–жҳҜеҜ№е…¶еёҰжқҘзҡ„еҘ‘жңәзҡ„иөһзҫҺпјҢиҝҳжҳҜеҗҺжқҘеҺҶеҸІеӯҰиҖ…иөӢдәҲе…¶ж”№еҸҳзҫҺеӣҪеҚ—йғЁеҺҶеҸІең°дҪҚзҡ„и®әиҝ°пјҢйғҪд»ӨиҝҷдёӘе°Ҹе°Ҹзҡ„жҳҶиҷ«иғҢиҙҹдәҶиҝҮеӨҡж— еҠӣжүҝжӢ…зҡ„еҺҶеҸІиҙЈд»»гҖӮжҜ«ж— з–‘й—®пјҢд»Һ1892е№ҙиө·пјҢе®ғжҲҗдёәзҫҺеӣҪеҚ—йғЁеҺҶеҸІжј”еҢ–иҝҮзЁӢзҡ„з§ҜжһҒеҸӮдёҺиҖ…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еңЁжҹҗз§ҚзЁӢеәҰдёҠпјҢеҰӮзҫҺеӣҪеҚ—йғЁзҺҜеўғеҸІе®¶и©№е§Ҷж–ҜВ·еҗүжЈ®еңЁе…¶еҮәзүҲдәҺ2011е№ҙзҡ„и‘—дҪңгҖҠ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и“қи°ғгҖӢдёӯжүҖиЁҖпјҢ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д№ӢдәҺзҫҺеӣҪеҚ—йғЁзӨҫдјҡгҖҒж–ҮеҢ–гҖҒз»ҸжөҺгҖҒж—ҸзҫӨе…ізі»зҡ„ж”№еҸҳпјҢе…¶иұЎеҫҒж„Ҹд№үеӨ§дәҺе®һйҷ…еҪұе“ҚгҖӮеҪ“дәә们еңЁдёҚж–ӯејәи°ғ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дҪңдёәвҖңйӮӘжҒ¶д№ӢжіўвҖқзҡ„еӯҳеңЁж—¶пјҢе®һиҙЁдёҠжҳҜеңЁиҜ•еӣҫиҪ¬е«ҒзҒҫйҡҫзҡ„дәәдёәиҙЈд»»пјҢжҲ–е°Ҷд№Ӣи§ҶдёәвҖңдёҠеёқд№ӢдёҫвҖқзҡ„еӨ©и°ҙпјҢжҲ–е°Ҷд№Ӣж–ҘдҪңиҮӘ然зҡ„жҠҘеӨҚпјҢд»ҺиҖҢжҠ№жқҖ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еңЁд»ҺжҳҶиҷ«еҸҳжҲҗе®іиҷ«гҖҒеҸҳжҲҗжЈүиҠұзҳҹз–«зҡ„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з§Қж—Ҹдё»д№үгҖҒиө„жң¬дё»д№үз»ҸжөҺгҖҒеңҹең°еҲҶй…ҚеҲ¶еәҰд»ҘеҸҠз”ҹжҖҒз ҙеқҸжүҖжү®жј”зҡ„и§’иүІгҖӮеңЁеҗүжЈ®зҡ„вҖңи“қи°ғвҖқдёӯпјҢ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жҳҜдёҖдёӘејәжңүеҠӣзҡ„йҹіз¬ҰпјҢз”ҡиҮіжҳҜдёҖж®өиҮӘжҲҗжӣІи°ғзҡ„д№җз« пјҢдҪҶжҳҜе®ғд»Қ然仅жҳҜе…¶дёӯзҡ„дёҖдёӘйғЁеҲҶгҖӮеҶ…жҲҳеҗҺеҚ—йғЁзҡ„еҺҶеҸІе№¶дёҚжҳҜдёҖйғЁ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еҸІпјҢжӯЈеҰӮдәәзұ»еҺҶеҸІд№ҹж— жі•иў«иҝҳеҺҹжҲҗд»»дҪ•дёҖйғЁеҚ•дёҖеӣ зҙ зҡ„еҺҶеҸІпјҢж— и®әжҳҜзҳҹз–«еҸІгҖҒйЈҹзү©еҸІпјҢиҝҳжҳҜз§Қж—ҸеҸІгҖҒжҖ§еҲ«еҸІгҖӮиҷҪ然еҪ“жҲ‘们宣称дәәзұ»еҺҶеҸІе°ұжҳҜдёҖйғЁжҹҗжҹҗеҸІзҡ„ж—¶еҖҷпјҢеҸҜд»Ҙи®Іиҝ°дёҖдёӘеҰӮеҗҢеӣ зү№жҷ®иҺұж–ҜеҹҺйӮЈиҲ¬йІңдёәдәәзҹҘиҖҢеҸҲе……ж»ЎжҲҸеү§еҢ–зҡ„ж•…дәӢпјҢдҪҶжҳҜж•…дәӢз»Ҳ究仅жҳҜж•…дәӢпјҢж— жі•ж¶өзӣ–еҺҶеҸІзҡ„еӨҚжқӮжҖ§пјҢжӣҙж— жі•жӣҝд»ЈеҹәдәҺеӨҚжқӮжҖ§еҲҶжһҗиҖҢжҸҗеҮәзҡ„еҺҶеҸІи§ЈйҮҠгҖӮ
дёҺйӮЈдәӣиҝҮеҲҶејәи°ғ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еҪұе“Қзҡ„еҺҶеҸІеӯҰиҖ…зӣёжҜ”пјҢжӣҙеӨҡзҡ„еҺҶеҸІеӯҰиҖ…иө°еҗ‘дәҶеҺҶеҸІиҝҳеҺҹи®әзҡ„еҸҰдёҖйқўвҖ”вҖ”еҝҪи§Ҷ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д»ҘеҸҠиҮӘ然дёҺдәәзұ»еҺҶеҸІд№Ӣй—ҙзҡ„зӣёдә’еҪұе“ҚгҖӮ2015е№ҙпјҢе“ҲдҪӣеӨ§еӯҰеҺҶеҸІеӯҰж•ҷжҺҲж–Ҝж–ҮВ·иҙқе…Ӣзү№еҮәзүҲгҖҠжЈүиҠұеёқеӣҪпјҡдёҖйғЁиө„жң¬дё»д№үе…ЁзҗғеҸІгҖӢдёҖд№ҰпјҢеӣҠжӢ¬еҢ…жӢ¬зҫҺеӣҪеҺҶеҸІеӯҰжңҖй«ҳеҘ–зҸӯе…ӢжҙӣеӨ«зү№еҘ–еңЁеҶ…зҡ„иҜёеӨҡеӣҫд№ҰеҘ–пјҢжҲҗдёәеҪ“еӯЈзғӯй—ЁгҖӮжӯӨд№Ұе°ҶзҫҺеӣҪеҺҶеҸІзҡ„з»Ҹе…ёи®әйўҳеёҰе…Ҙе…ЁзҗғеҸІзҡ„и§ҶйҮҺеҪ“дёӯпјҢж—ўд»ЈиЎЁдәҶиө„жң¬дё»д№үеҸІзҡ„еӨҚе…ҙпјҢеҸҲж Үеҝ—зқҖзҫҺеӣҪеҸІе…ЁзҗғеҢ–еҸҷдәӢзҡ„еҙӣиө·пјӣж— и®әд»Һж—¶й—ҙе°әеәҰиҝҳжҳҜз©әй—ҙи·ЁеәҰпјҢйғҪиҝңиҝңи¶…и¶ҠдәҶзҫҺеӣҪеҚ—йғЁжүҖиғҪж¶өжӢ¬зҡ„жҖқиҖғпјҢжһ„е»әдәҶдёҖйғЁж°”еҠҝжҒўе®Ҹзҡ„иө„жң¬дё»д№үжү©еј еҸІгҖӮ
然иҖҢпјҢеңЁдёҖдёӘзҺҜеўғеҸІеӯҰиҖ…зңӢжқҘпјҢиҝҷжҳҜдёҖйғЁд»ӨдәәеӨұжңӣзҡ„и‘—дҪңгҖӮиҙқе…Ӣзү№еңЁеҜји®әдёӯеҶҷйҒ“пјҡвҖңиҝҷз§ҚиҪ»жҹ”жқҫиҪҜзҡ„зҷҪиүІзәӨз»ҙеҚ жҚ®жӯӨд№Ұзҡ„дёӯеҝғең°дҪҚвҖқпјҢиҖҢдәӢе®һдёҠпјҢеңЁиҝҷйғЁз”ұжЈүиҠұеҲӣйҖ зҡ„еёқеӣҪе…ҙдәЎеҸІдёӯпјҢжңүжЈүиҠұз§ҚжӨҚиҖ…гҖҒжЈүиҠұзәәз»ҮиҖ…гҖҒжЈүиҠұз»ҸиҗҘиҖ…пјҢжңүжңәеҷЁгҖҒеҲ¶еәҰгҖҒйҮ‘й’ұгҖҒеӣҪ家пјҢжңүиө„жң¬дё»д№үдёҚж–ӯеҸҳиҝҒеҚҙе§Ӣз»Ҳиў«жё…жҷ°е‘ҲзҺ°зҡ„йқўзӣ®пјҢе”ҜзӢ¬жІЎжңүжЈүиҠұпјҢжӣҙжІЎжңүдёҺжЈүиҠұжҒҜжҒҜзӣёе…ізҡ„еӨҚжқӮз”ҹжҖҒеңҲвҖ”вҖ”ж°ҙгҖҒеңҹеЈӨгҖҒж°”еҖҷгҖҒжӨҚиў«гҖҒеҠЁзү©гҖҒеҫ®з”ҹзү©гҖӮдҪҶжӯЈжҳҜиҝҷдәӣжңүжңәзү©дёҺж— жңәзү©пјҢд»ӨдёҖз§ҚеҚ•дёҖдҪңзү©зҡ„з§ҚжӨҚжҲҗдёәеҸҜиғҪпјӣиҖҢз”ҹжҖҒеңҲзҡ„еҸҳиҝҒеҸҲдёҚж–ӯең°еҲ¶зәҰгҖҒйҮҚжһ„зқҖжЈүиҠұеёқеӣҪпјҢжҢ«зЈЁе…¶дёҖеҫҖж— еүҚзҡ„дҝЎеҝғгҖӮеҜ№иҙқе…Ӣзү№иҖҢиЁҖпјҢжүҖи°“еҚ жҚ®дёӯеҝғзҡ„жЈүиҠұжҳҜз§ҚжӨҚеӣӯдёӯзҡ„дҪңзү©пјҢжҳҜиҪ§жЈүжңәдёӯзҡ„зәӨз»ҙпјҢжҳҜзәәзәұеҺӮзҡ„дә§е“ҒпјҢеҚҙдёҚжҳҜз»ҸеҺҶдәҶдёҖеҚғдёҮиҮідёӨеҚғдёҮе№ҙзҡ„жј«й•ҝжј”еҢ–пјҢеңЁдёҚеҗҢж—¶з©әдёӯеҚ жҚ®дёҚеҗҢз”ҹжҖҒдҪҚзҡ„пјҢдҪңдёәдёҖз§ҚжӨҚзү©иҖҢз”ҹй•ҝзҡ„з”ҹе‘ҪгҖӮеңЁжЈүиҠұиў«иөӢдәҲдёҖеҲҮеҸҜиғҪзҡ„зӨҫдјҡеұһжҖ§ж—¶пјҢе®ғзҡ„иҮӘ然еұһжҖ§иў«еүҘзҰ»з”ҡиҮійҒ—еҝҳгҖӮ
иҜҡеҰӮиҙқе…Ӣзү№жүҖиЁҖпјҡвҖңиҝҷз§ҚжӨҚзү©иҮӘиә«ж— жі•еҲӣйҖ еҺҶеҸІгҖӮвҖқдҪҶжҳҜпјҢиҝҷ并дёҚж„Ҹе‘ізқҖиҝҷз§ҚжӨҚзү©иҮӘиә«дёҚе…·еӨҮеҺҶеҸІпјҢиҝңеңЁдәәзұ»еҮәзҺ°д№ӢеүҚпјҢе®ғдҫҝеңЁе…¶з”ҹжҖҒдҪҚдёӯдёҠжј”зқҖдёҖйғЁе…ідәҺзү©з§Қеӯҳз»ӯгҖҒз№Ғж®–гҖҒз«һдәүзҡ„жј”еҢ–еҸІгҖӮдҪҶжҳҜеҜ№еҺҶеҸІз ”究иҖ…иҖҢиЁҖпјҢеҰӮжӯӨжј”еҢ–еҸІйҖёеҮәиҮӘе·ұзҡ„зҹҘиҜҶжЎҶжһ¶дёҺдё“дёҡи®ӯз»ғпјҢе®үе…Ёзҡ„еҒҡжі•жҳҜйҖҖеӣһж–ҮеҢ–еҲҶжһҗзҡ„дј з»ҹеҪ“дёӯпјҢи®Іиҝ°жЈүиҠұзҡ„ж–ҮжҳҺеҸІгҖӮж— и®әе…¶еҲҶжһҗзҡ„еҸ–еҫ„жҳҜеҚ—йғЁж №ж·ұи’Ӯеӣәзҡ„з§Қж—Ҹдё»д№үдёҺзҷҪдәәиҮідёҠпјҢжҠ‘жҲ–иЎҖи…Ҙзҡ„жҲҳдәүиө„жң¬дё»д№үд№Ӣе…ҙиө·е’Ңж°‘ж—ҸеӣҪ家зҡ„е»әжһ„пјӣж— и®әжҳҜеұҖйҷҗдәҺ1919е№ҙеӣ зү№жҷ®иҺұж–ҜеҹҺзҡ„дёӘжЎҲз ”з©¶пјҢиҝҳжҳҜи·Ёи¶Ҡж—¶з©әзҡ„е®ҸеӨ§еҸҷдәӢпјҢз©¶е…¶ж №жң¬пјҢйғҪжҳҜдёҖз§Қз®ҖеҚ•еҢ–зҡ„еҺҶеҸІи§ЈйҮҠпјҢеӣһйҒҝдәҶеҺҶеҸІзҡ„еӨҚжқӮжҖ§пјҢеӣһйҒҝдәҶзҺ°д»ЈиҮӘ然科еӯҰеҜ№еҺҶеҸІеӯҰ家жҖқз»ҙж–№ејҸзҡ„жҷәжҖ§жҢ‘жҲҳгҖӮ
еңЁзҺ°д»ЈиҮӘ然科еӯҰдёӯпјҢеҜ№еҺҶеҸІеӯҰиҖ…иҖҢиЁҖпјҢжңҖе…·еҗҜеҸ‘жҖ§зҡ„зҗҶи®әд№ӢдёҖжҳҜиҫҫе°”ж–Үзҡ„иҮӘ然演еҢ–еӯҰиҜҙгҖӮиҫҫе°”ж–ҮеңЁиҮӘ然дёӯеҸ‘зҺ°дәҶеҺҶеҸІпјҢд»–зҡ„еҗҺ继иҖ…们еҲҷеңЁиҮӘ然дёҺж–ҮеҢ–зҡ„еҚҸеҗҢжј”еҢ–дёӯеҸ‘зҺ°дәҶдәҢиҖ…иҮӘжҷәдәәзү©з§ҚиҜһз”ҹд»ҘжқҘдҫҝжңӘжӣҫеҲҶеүІзҡ„зә з»“иҒ”зі»гҖӮеңЁеҺҶеҸІеӯҰ家е”җзәіеҫ·В·жІғж–Ҝзү№зңӢжқҘпјҢзҺҜеўғеҸІеҫ—д»ҘжҲҗз«ӢпјҢе…¶дёҖеңЁдәҺдәәзұ»дёҺиҮӘ然其дҪҷйғЁеҲҶзҡ„еҚҸеҗҢжј”еҢ–пјҢе…¶дәҢеҲҷеңЁдәҺдәҢиҖ…е…ұеҗҢз»ҸеҺҶзҡ„и„ҶејұжҖ§гҖӮзҫҺеӣҪзҺҜеўғеҸІе®¶еҹғеҫ·и’ҷВ·зҪ—зҙ еңЁе…¶еӨ§дҪңгҖҠжј”еҢ–еҸІпјҡз»“еҗҲеҺҶеҸІдёҺз”ҹзү©д»ҘзҗҶи§Јең°зҗғдёҠзҡ„з”ҹе‘ҪгҖӢдёӯжҸҗеҮәдәҶвҖңжј”еҢ–еҸІвҖқзҡ„жҰӮеҝөпјҢд»–е°Ҷд№ӢжҰӮжӢ¬дёәеӣӣдёӘж–№йқўпјҡ第дёҖпјҢдәәзұ»еҪұе“ҚдәҶиҮӘиә«е’Ңе…¶д»–зү©з§Қзҡ„ж•°йҮҸпјӣ第дәҢпјҢдәәзұ»еј•еҸ‘зҡ„жј”еҢ–еҪўеЎ‘дәҶдәәзұ»еҺҶеҸІпјӣ第дёүпјҢдәәзұ»дёҺйқһдәәзұ»зҫӨдҪ“еҚҸеҗҢжј”еҢ–пјҢжҲ–иҖ…иҜҙжҢҒз»ӯең°зӣёдә’еҪұе“Қпјӣ第еӣӣпјҢжҜ”д№ӢеҚ•зӢ¬зҡ„еҺҶеҸІеӯҰжҲ–иҖ…з”ҹзү©еӯҰпјҢжј”еҢ–еҸІиҝҷдёӘж–°еӯҰ科еҸҜд»Ҙеё®еҠ©жҲ‘们жӣҙеҘҪең°зҗҶи§ЈиҝҮеҺ»е’ҢеҪ“дёӢгҖӮ
е…ідәҺеҚҸеҗҢжј”еҢ–пјҢжңҖз»Ҹе…ёзҡ„иҢғдҫӢиҺ«иҝҮдәҺ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дёҺжқҖиҷ«еүӮгҖӮз”ұдәҺеӨ§йқўз§Ҝзҡ„еҚ•дёҖз§ҚжӨҚпјҢеј•еҸ‘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зҡ„ж•°йҮҸзҲҶзӮёпјҢд»ҺиҖҢеҲәжҝҖжқҖиҷ«еүӮзҡ„е№ҝжіӣдҪҝз”ЁгҖӮ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еңЁз¬¬дёҖд»ЈжқҖиҷ«еүӮдҪҝз”ЁеҗҺдә§з”ҹжҠ—дҪ“пјҢе№ёеӯҳдёӢжқҘзҡ„жҳҶиҷ«зҡ„еҗҺиЈ”жҗәеёҰиҝҷз§ҚжҠ—дҪ“пјҢиҝ«дҪҝеҢ–еӯҰиҚҜеүӮе…¬еҸёжҺЁеҠЁжҠҖжңҜжј”еҢ–пјҢеҚҮзә§е…¶дә§е“ҒпјҢеҪўжҲҗдәҶжҳҶиҷ«жҠ—дҪ“вҖ”жқҖиҷ«еүӮзҡ„еҚҸеҗҢжј”еҢ–гҖӮеҖјеҫ—жіЁж„Ҹзҡ„жҳҜпјҢеҰӮжӯӨжј”еҢ–并йқһжҳҜеңЁдәҢиҖ…д№Ӣй—ҙиҝӣиЎҢзҡ„е°Ғй—ӯеӣһи·ҜпјҢиҖҢжҳҜеҪўжҲҗе·ЁеӨ§зҡ„з”ҹжҖҒдёҺж–ҮеҢ–жј”еҢ–зҪ‘з»ңгҖӮз”ҹжҖҒзҪ‘з»ңзҡ„и®®йўҳжҳҜи•ҫеҲҮе°”В·еҚЎжЈ®гҖҠеҜӮйқҷзҡ„жҳҘеӨ©гҖӢдёӯи®Ёи®әзҡ„дёӯеҝғй—®йўҳпјҢи®Іиҝ°дәәзұ»зү©з§ҚеҰӮдҪ•дёҺиҮӘ然з•Ңе…¶д»–зү©з§Қд»ҘеҸҠж— жңәзү©еҲҶжӢ…еҗҢж ·зҡ„зҺҜеўғйЈҺйҷ©гҖӮиҖҢдёҺз”ҹжҖҒзҪ‘з»ңзӣёдә’еҪұе“Қзҡ„ж–ҮеҢ–зҪ‘з»ңзҡ„жј”еҢ–пјҢжӯЈжҳҜеҺҶеҸІеӯҰиҖ…зҡ„з ”з©¶иҜҫйўҳгҖӮеңЁжӯӨеҚҸеҗҢжј”еҢ–дёӯпјҢдёҚеҗҢж—¶й—ҙгҖҒз©әй—ҙгҖҒз”ҹжҖҒдёӯзҡ„жқғеҠӣз»“жһ„дёҺиҙўеҜҢеҲҶй…ҚйғҪеңЁеҸ‘з”ҹзқҖж”№еҸҳгҖӮжЈүй“ғиұЎйј»иҷ«дёҚд»…жҳҜдёҖз§Қз¬ҰеҸ·пјҢжҲ–жҳҜз©әз©ҙжқҘйЈҺзҡ„з„Ұиҷ‘пјҢе®ғеҗҢж ·жҳҜзңҹе®һзҡ„зү©иҙЁжҖ§еӯҳеңЁпјҢе…¶иғҢеҗҺжҳҜдёҖз§Қ并йқһз”ұдәәзұ»жүҖеҲӣйҖ зҡ„ејәеӨ§еҠӣйҮҸпјҢдёҺжқҖиҷ«еүӮгҖҒиҪ§жЈүжңәгҖҒиө„жң¬дё»д№үгҖҒз§Қж—ҸеҺӢиҝ«дёҖйҒ“е…ұеҗҢеҪұе“ҚдәҶжЈүиҠұеёқеӣҪдёҺзҫҺеӣҪеҚ—йғЁзҡ„еҺҶеҸІгҖӮ
д»Ҡж—ҘпјҢеҪ“ж–°еҶ иӮәзӮҺе°ҶзҺ°д»ЈзӨҫдјҡзҪ®дәҺжҒҗж…ҢдёҺз„Ұиҷ‘еҪ“дёӯпјҢжҲ‘们дёӯзҡ„еҫҲеӨҡдәәејҖе§Ӣж„ҸиҜҶеҲ°иҮӘ然еңЁз”ҹжҙ»дёӯзҡ„ејәеӨ§еӯҳеңЁгҖӮиә«дёәеҺҶеҸІеӯҰиҖ…пјҢйңҖиҰҒз”Ёд»Ҡж—Ҙзҡ„жҷәж…§йҮҚж–°еҗҜеҸ‘еҜ№еҺ»ж—Ҙд№ӢеҸІзҡ„и®ӨзҹҘпјҢи®ӨиҜҶж–ҮеҢ–дёҺиҮӘ然еҚҸеҗҢжј”еҢ–зҡ„еӨҚжқӮеҺҶеҸІгҖӮе”ҜжңүжӯӨпјҢж–№иғҪзңҹжӯЈе®ҡд№үдәәзұ»зҡ„иҝҮеҫҖдёҺзҺ°еңЁпјҢдәәзұ»зҡ„ж –жҒҜд№Ӣең°пјҢд»ҘеҸҠдәәзұ»иҮӘиә«гҖӮ
пјҲдҪңиҖ…пјҡдҫҜж·ұпјҢзі»дёӯеӣҪдәәж°‘еӨ§еӯҰеҺҶеҸІеӯҰйҷўеүҜж•ҷжҺҲпј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