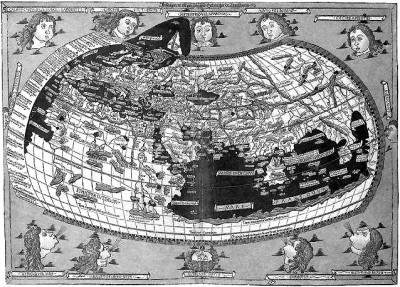文明史书写在西方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启蒙时期出现了反映欧洲社会进步的“文明”概念,自此欧洲人有意识地运用这一概念书写文明史。由于“文明”概念蕴含着欧洲社会的价值取向,以此为基础书写的文明史便不同程度地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这以19世纪的文明史著作最为典型。20世纪上半叶,世界大战对西方社会造成的冲击使得一些学者开始怀疑线性进步史观,由此出现了以文明形态史观来书写的文明史。20世纪下半叶,威廉·麦克尼尔等全球史学者在撰写全球文明史时,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由此开始了全球史观下的文明史书写。这种文明史实现了从历时性谱系解释向共时性互动维度思考的转变,亦即“空间转向”,代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史书写的一种新趋势。
一
一般认为,西方的“文明”一词出现于1756年,由法国思想家密拉波首先使用,随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流行开来。起初这个词只有单数形式,用来指欧洲人所达到的一种社会状态。到19世纪20年代,欧洲学者开始将“文明”用于描述其他民族或社会,由此出现了复数用法。复数意义的“文明”运用于历史书写,则出现了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文明史”。
“文明”一词之所以在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出现并流行开来,除了欧洲社会自身发展这一因素外,也与欧洲人的海外扩张密不可分。此时的欧洲人随着其扩张步伐遍布世界,殖民者、探险家、传教士、旅行者等将其海外见闻记载下来,使生活于欧洲的知识分子足不出户也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形态。正是这些进入欧洲人视野的“他者”,促使欧洲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具有文化优越感的“文明”意识。美国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由此称产生于欧洲的这种“文明”观念既是一种欧洲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殖民意识形态。19世纪欧洲的文明史书写,明显受到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这种“文明”概念源于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历史经验,是当时欧洲人在进步观影响下充满了文化优越感的一种自我表述。在欧洲文明史家眼里,“文明”是欧洲社会不断进步的结果,是欧洲社会在物质和精神上所达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他们认为,海外其他民族和社会仍然处于“蒙昧”或“野蛮”状态。由此,“文明”观念也成了一种殖民意识形态。在此观念影响下,文明史家在描写处于不同社会状态的世界各民族时,以欧洲社会进步的尺度来衡量,将各民族的社会差异转换成时间维度的叙事,如此,文明史中从蒙昧、野蛮到文明的等级差异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处于“文明”状态的欧洲社会成了其他各“野蛮”民族前进的方向。这种文明史赋予了欧洲殖民扩张中的“文明使命”以历史合理性。毫无疑问,19世纪欧洲“文明”观念之下的文明史,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
以法国基佐和古斯塔夫·杜库雷的文明史为例。基佐在《欧洲文明史》(1828)中声称“文明”包含两个要素:社会的进步和个体的进步,或者说社会制度的改善和人类智力的发展。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这两个方面得到了发展,“那里的人们便宣告和欢呼‘文明’的到来”。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是从进步史观出发,以欧洲为例对这种“文明”概念做了一种历史诠释。杜库雷的《文明简史》(1886)沿袭了基佐的文明观,认为文明即是人类在政治、社会、经济、智力和道德上的整体发展。该书在简要概述了尼罗河和两河流域的古代民族之后,重点讲述了希腊和罗马文明、欧洲中世纪、自文艺复兴至18世纪的“现代”欧洲,以及从法国革命到19世纪的“当代”欧洲,最后一章标题为“欧洲文明传遍世界”。作者声称:“在我们这个时代,欧洲人正在使非洲和亚洲得到再生。始于东方的文明又回到了东方,完成了一个奇妙的循环。光来自东方,但正是西方把它带回给东方,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灿烂。”这种叙事将人类文明史写成了一部欧洲文明谱系的演变史,在以进步史观来凸显欧洲文明的优越性时,也将欧洲殖民扩张史粉饰成了一部欧洲人履行“文明使命”的历史。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间的战争打破了欧洲文明优越的神话,文明呈线性进步且由欧洲代表最高水平的文明观开始动摇。与此同时,社会有机论的流行也使人们将“文明”看作是一种有着兴衰周期的有机体。于是,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每一种“文明”都有其自身兴衰的过程,西方文明也不例外。这样,出现了文明形态史观影响下的文明史书写。斯宾格勒认为世界上有8种自成体系的文明,汤因比则将世界历史上的文明概括为26个,进一步丰富了斯宾格勒提出的文明形态史观。随后,美国学者卡罗尔·奎格利在《文明的演进》中列举了世界历史上的16个文明,认为每个文明都经历了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普遍帝国、衰败和被入侵7个阶段的兴衰过程。此类文明史虽然把西方文明看作是人类诸多文明之一,不再将其看作是其他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归宿,但由于将各个文明割裂开来思考,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世界历史进程中西方文明与“他者”文明的关系问题。
二
1963年,西方世界中出现了两本颇具影响的文明史著作: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和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布罗代尔提出,文明是持续存在于一系列经济或社会之中不易发生渐变的某种东西,只能在长时段中进行研究,因此文明史是一种长波的历史。布罗代尔还认为,“每种文明都会引进和输出其文化的某些方面”,由此造成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不过,这种观点在《文明史纲》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全书仍以不同文明区域的独立叙事为主。显然,时间维度的历史变迁仍然是布罗代尔思考文明史的主要路径。
麦克尼尔在思考文明之间的关系方面,比布罗代尔迈出了更大步伐。他将西方放在世界历史框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中来书写,强调文明互动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由此奠定了文明史书写的全球史框架。
随着20世纪末全球史的兴起,一些西方学者越来越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例如,美国学者皮特·斯特恩斯等编纂的《全球文明史》(1992)和菲利普·费尔南徳兹-阿迈斯托的《文明》(2001),都将文明互动作为文明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来书写,世界文明史不再是叙述各个文明独立发展的历史。中国学者也对书写这种文明史做了有益探索。例如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2004)对不同文明的交流给予了极大关注,认为“文明在纵向发展的同时,横向上也在相互运动。这是使文明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学者大卫·威尔金森曾提出文明是一种世界体系,由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区域构成,世界历史就是半边缘或边缘文明不断融入中心文明的过程。与此同时,麦克尼尔将西方文明置于整个世界历史中来审视的研究视角,也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例如,斯特恩斯的《世界历史上的西方文明》(2003)探讨了如何从全球视角来理解西方文明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批评了以往西方文明史教材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4)将西方文明置于与东方的互动关系中来理解,反驳了西方的欧洲中心论神话。这些强调文明互动的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叙事。
这种文明史书写的新趋势,是历史学“全球转向”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空间转向”,是以全球史视角和方法来书写文明史,实现了历史叙事的轴心从历时性谱系向共时性关系的转变,打破了文明间边界的局限,从关联、互动、体系等视角来理解文明的变迁,由此达到以横向空间维度的思考来补充和丰富纵向时间维度的内源性解释。
如上所述,文明史书写出现“空间转向”,与全球史的兴起密不可分。全球史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兴起之时,“文明”是其中重要的研究单位,文明互动受到高度关注。威廉·麦克尼尔等人早期的全球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明史。正是全球史视角、理论和方法的介入打破了以往文明史的局限,把文明史发展成为一种以多元文明互动为主题的历史,并以此消解文明史书写中的西方中心论。刘新成在《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一文中提出,全球史兴起之前西方的文明史可分为两种类型,即“文明价值理论”派生的“进步史观”影响下的文明史和“文明类型理论”派生的“平行史观”影响下的文明史,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而“全球史观的‘文明互动说’为化解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观的内在矛盾、廓清人类文明的统一性与差异性问题,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
(作者:刘文明,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