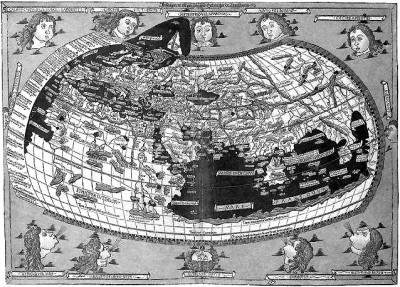瘟疫犹如“行走的生化武器”,与人类文明如影随形。古罗马世界也同样遭受了不绝于书的瘟疫之殇。经检索可知,从帝国初期的李维到6世纪的普罗柯比等近70位作家,记录了130余次罗马人关于瘟疫的痛苦记忆。这些记述大多简短,很少详细说明瘟疫的特征、范围、后果及应对;加之古典作家并没有细菌、病毒的概念,无法对多次传染病的病原体做出区分,通常把多数难以治愈、致命性强的流行病统称为瘟疫(“loimoi”或“lues”,意为“死亡率高”),这给后世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
随着近年来环境史、疾病史研究的兴起以及新近环境考古分子技术的运用,关于古罗马的瘟疫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以邓肯·琼斯为代表的学者们发现,疟疾在罗马和意大利地区多次暴发,甚至长期成为罗马人的头号杀手。更为重要的发现是,罗马帝国时期还暴发过三场世界性的大瘟疫,它们分别是:极可能是天花的安东尼瘟疫(165-180年)、很可能是线状病毒出血热的西普里安瘟疫(251-270年)和地中海世界的首次黑死病—查士丁尼瘟疫(541-543年)。
古罗马时期为什么会暴发多次大规模瘟疫呢?美国学者凯尔·哈珀认为,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50年是“罗马最优气候期”。这一时期气候温暖、湿润,适于扩大生产和建设。罗马人滥伐森林、开荒垦地,加大粮食生产;扩建城市,容纳聚集人口;修路挖渠,改道河流、开埠通商等改变地形地貌的活动,使生态系统变得脆弱不堪。加之世界性海陆商贸体系网的逐步建立,使得疾病和商品一同流通,形成了麦克尼尔所说的“文明化疾病池的汇聚”。至公元2世纪中期,地中海地区进入“小冰河期”,气候变得寒冷、干燥,人类继续破坏自然的行为超过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因而出现了干旱、饥荒、传染病和战争等轮番上演的局面。尤其是,来自外部的致命病原体让缺乏免疫力的罗马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些大瘟疫“就像火焰一样”在帝国各省蔓延,很多人悲惨地死去。因古代文献缺乏与表述模糊,我们很难获得每次瘟疫期间受难人口的精确数据。据研究,源自帕提亚的安东尼瘟疫导致帝国人口死亡率约为22%-24%(1650万-1800万);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普里安瘟疫使亚历山大里亚人口从约50万锐减到19万;从埃及传入的查士丁尼瘟疫则造成帝国至少有1/3的人口死亡。瘟疫期间,整个社会处于混乱和失序状态,人间悲苦难以名状。有人因极度恐惧而四处逃散,不顾亲友;有人失去理智,疯狂寻找“肇事者”,追寻瘟疫的源头。
在盛行神灵崇拜的罗马社会,宗教首先需要对之做出回应。然而,祭司们通常的解释是,瘟疫是神对人类恶行的惩罚(即天谴论),解决方法是平息神怒。此时,既能制造瘟疫也能治愈瘟疫的阿波罗最受欢迎。在安东尼瘟疫和西普里安瘟疫期间,整个帝国社会转向了古老的阿波罗崇拜。据考古发现,一些行省竖起手持弓箭“抵挡邪恶的阿波罗”神像,很多金币上也铸有“治愈者阿波罗”的形象,以及各种刻有阿波罗神谕的石碑、护身符等。多神信仰在应对瘟疫时并未起到有效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基督教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基督教同样把瘟疫的暴发归因于威严上帝对人类作恶的降罪。首任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为此还精心组织祈求上帝宽恕和庇佑的大型祈祷仪式,这种做法很快传遍欧洲。
在求神无果后,医学又无法做出有效解释的社会很容易把突然暴发的瘟疫归咎于人祸。文献资料表明,罗马人对瘟疫“人祸”的追责是极具戏剧性的,其中既有对女性和囚犯等弱势群体的污化,也有政治抹黑事件,还有宗教迫害等。李维提到公元前329年的罗马瘟疫时记述了所谓“主妇投毒”事件,“投毒”的这位主妇被当众处决。图密善时期的罗马瘟疫被归咎于罪犯用毒针袭击民众。官方对安东尼瘟疫的说法是,反叛的叙利亚将军阿维狄乌斯洗劫塞琉西亚的“长发阿波罗”圣所而招致阿波罗的报复。关于西普里安瘟疫的说辞,德西乌斯皇帝谴责基督徒因拒绝参加国家献祭,招致众神降罪,于是首次开动国家机器镇压基督教徒;在这次迫害中,殉教的西普里安教父等人则认为瘟疫是上帝对当局迫害基督徒的惩罚。显而易见,这些为寻找替罪羊,不同群体间相互攻讦、施暴的做法,只能暂时转移民众视线,不但于消除瘟疫无益,而且会加重疫情。
除了上述非理性的解释和追责外,罗马各阶层也尽力采取各种应急措施,以维持社会的基本运转,如安葬亡者、救助生者、灾后重建等。尽管相关文献资料仅零星留存,却也闪耀着罗马人在面对可怕的瘟疫时所表现出的责任、怜悯和不屈等人性的光辉。
瘟疫期间,当务之急是要防止疾病进一步扩散,处理带有病源的尸体。皇帝马可·奥利略颁布了严格的殡葬法令,规定包括贵族在内的所有市民禁止在罗马城内埋葬尸体,必须运到城外焚化后埋葬。为此,政府安排四轮或两轮马车把城里尸体运到城外集中安葬。考古学家在古底比斯发现了瘟疫期间集体焚尸的墓地(埋有1330具尸体)和用石灰水大面积消毒的痕迹。马可·奥利略还为不幸丧生的德高望重的贵族塑像,为底层死者举行集体葬礼。皇帝加卢斯和沃卢西亚努斯为所有贫穷的死者安排了体面的葬礼。查士丁尼命令其秘书狄奥多罗斯负责疫情下的尸体处理。后者重金雇佣健康平民将无人认领的尸体运至城外深埋,甚至命人在城外高山上挖掘了可放置七千多具尸体的坟墓。当政者的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控制了疾病的扩散,也赢得了民众的信任。
死者已去,生者尚需救助。首先是赈灾救困,治病救人。马可·奥利略曾在瘟疫期间为市民分发粮食和救助金。查士丁尼皇帝曾出动军队维持开仓赈济饥民和发放救济金的秩序,还把剧院和赛马场设为临时医院和避难场所。教会早期的医院和慈善机构也承受着护理和救助受难民众的巨大压力。普罗柯比曾说,“照顾和治疗病人的那些人则感到持续的疲惫不堪,感染死亡者很多……所有人对他们的同情不亚于对患者的同情”。
面对未知又致命的瘟疫,罗马医生虽然束手无策,仍无畏地探索病因和救治病患。医学家盖伦提出了瘟疫是由瘴气中的“疾病种子”感染易感人群的理论,为19世纪细菌论的出现提供了理论支持。作为瘟疫的亲历者,他声称治愈了无数患者,并将基本符合天花病毒特征的临床观察记录在《医学方法》中。书中还介绍了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通过点燃带有香味的大火堆驱除瘟疫的方法。君士坦丁堡的医生为查明病灶而冲破宗教阻力解剖尸体,结果在腹股沟发现一种痈疽,即腺鼠疫的典型症状。而且,他们都主张对病患进行基本护理与生活照料。医学研究表明,即便没有药物,这些帮助也至少能减少2/3以上的死亡率。
当疫情缓解或过去后,灾后重建成为社会继续运转的关键。由于瘟疫造成雅典等多个城市的司法系统瘫痪,马可·奥利略曾写信要求当地人放宽最高法官候选人的资格限制。为应对士兵大量死亡和北部蛮族伺机入侵的危机,他拍卖皇室珠宝,出资训练奴隶、征召角斗士和武装强盗等,以补充兵源。面对城乡物价飞涨、陷入瘫痪的窘状,查士丁尼出台遏制物价的政策,并规定建筑工人、农民的工资不得超过平时的水平。为恢复农业生产,他还颁行了一项重新分配荒地的法律。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首都等地的困境,使社会得以维持基本的运转。
要言之,罗马人在多次肆虐的瘟疫面前,既有在神谴论认知下的非理性追责现象,又有朴素科学认识下的努力应对。无论如何,这正是罗马人面对恶魔般瘟疫所表现出的直面残酷现实而不屈服的“西西弗斯”精神。这种不懈的探索与抗争,也为后世的医学进步提供了理论知识和实践得失,增强了人们直面瘟疫的信心与希望。
(作者:姬庆红,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